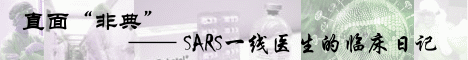
4月29日
昨天,接到通知,要求我们科里派人去SARS一线工作,本以为SARS与我们外科的关系不大,没想到,这次我们科居然需要抽调4个大夫去本院的SARS病房,可以想见,问题是多么严重。除了我们,科里还有3个护士参加全院90余人的医疗队,去老年病院开辟新的“战场”。据个人估算,目前我们医院在SARS一线的医护人员大约有220人左右,占了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1/4上下,看来北京市的疫情程度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得多。
今天上午,是上岗前的培训,包括疫情的介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进展还有传染病的个人防护。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诊断和治疗目前还不是十分确切。诊断方法还是使用排除法,还没有有效的诊断试剂;治疗也是以支持、抗病毒、抗感染为主,还没有确切的药物,主要还是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这也是所谓自限性疾病的原因吧;另外SARS病人的医疗条件总的来说,还可以,但由于是传染病,对他们的心理关怀十分欠缺,有些病人表现出一些心理问题,不太配合治疗。
经过半天的培训和动员,我体会就是既要关心病人,治疗他们的疾病,共同战胜病魔,又要尽可能保护自己。动员会后,领导让我们各自留下手机号码,说6点钟等通知,最早的同志可能8点钟就要上岗……
我等到6点半,见没有人通知我,心想今天看来没我什么事了,我可以再回家一趟了。7点半,我刚进家门,刚看到儿子可爱的笑脸,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4月30日凌晨3点
刚从呼吸科SARS病房出来,洗完澡,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昨天晚上的情况还历历在目。
昨天,手机响后,尽然是医院SARS病房打来的,让我8点钟接班,这让我如何是好,但是,天大地大,唯SARS事大,况且据说在SARS病房的同志度日如年,那也只好如此了,我匆匆告别了妻儿,拿起业已准备好的电脑,走出了家门……
到了医院,先要到隔离区报道,但在隔离区,打听了许多人,方才找到我们医院的行政人员,原来因为SARS的缘故,他们也开始24小时排班,看来SARS已让全体总动员了。我们前前后后忙活了半天,才安排了房间及床铺,条件看来没有想象的好,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套被褥……耽误了好多时间,我好愧疚,还是要赶紧去接班,换了身上的衣服后,我便下了楼。
来到SARS病房门口,便被看门的护士长叫住,让我又换了衣服(这是专门用于进入SARS病房的内衣),然后戴口罩(口罩需要戴两副16层的棉口罩),然后戴帽子,然后要穿防化服(简称“喉服”,这是一种由防水塑料布制作的不透气的服装),然后需要穿3层鞋套,一切穿好后,再戴护目镜。护士长看过后,帮我拉开了门,这时我想起好象还应该有一个所谓“猪嘴口罩”,可问护士长,她无奈地摇摇头,现在这已经用完了,没办法,我终于进入了SARS病区。
SARS病区实在太安静了,尽能看到一两了工作人员想太空人一样,慢慢地移动(传染病房由于怕走路扬起灰尘,所以活动要尽可能地慢)。
上到4楼,与上一个大夫交了班,看他已经十分的疲倦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又穿上隔离衣,我进到SARS病房,我要去每一间病室巡视,我忽然迟疑了,真要和SARS接触了……这是一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在这里可能无处不在……接触传染,我可以不碰它;饮食传染,我可以不吃。但是空气传染,我无法不呼吸,空气无处不在,我无法不接触……太……进到4号病房,这是一名16岁的女孩,已经快痊愈了,看到她,我的心不那么紧了,我告诉她,她的胸片看起来很好,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了。10病房是一个74岁的老太太,她的病也不重,她一直央告我们要出去,说配老伴来看病,缺把自己留在这里住院。可她那里知道,她的老伴已在2天前去了,而她的儿子在同一天与父亲一起去了,儿媳妇和女儿正在地坛医院住院呢,我无言以对,只能敷衍……
时间不长,汗水已经湿透了里面的衣服,而且脚也开始痒,十分得痒……但是不能用手去挠,鼻子这时也开始痒,似有小虫钻人鼻孔,正是百爪挠心。赶紧翻阅病例,这时,眼罩上已蒙上了哈气,眼前白蒙蒙的,记录了病程,与护士交代了医嘱,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出来后,脱下隔离衣,看看钟,已经11点多了,再通过隔离门上的玻璃窗,护士还在里面忙碌着,她们甚至还要干原来卫生员的工作,因为由于害怕,雇的卫生员已经都跑光了,我感到护士们实在是太辛苦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外面有人敲门,接班的大夫来了,终于可以出去了,今天就可以过去了……
5月1日下午1点35分
今天班是2点到8点的,由于在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怕影响其它同志休息,我大约1点就去接班了,让上个班的同志早点儿回去休息,我也落个踏实。大约化了半个小时,换好衣服后,我接了班,小刘说今天情况不错,病人的病情比较稳定,随后他就下楼去了。我心想,看来今天运气要好的话,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果然,病人的情况比较好,只是偶尔有病人咳嗽,每每听到他们的这种声音,我的心都要揪起来,生怕他们会咳出血或憋着。和二线的大夫聊天,知道他们已在这里工作了近一个月了,他们好象并不是十分恐惧这种病,只是非常地想念家人,刘大夫有一个女儿,刚三岁,正是好玩的时候,由于怕把病传染给孩子,又需要隔离,刘大夫有快一个月没见着孩子和老公了,她说,她要一打电话就要近一个小时。我问她,我们来了,是否医院可能把他们替换下去,她说,可能没这个可能了,目前由于是综合医院改的SARS病区,他们算主要的技术力量,SARS是一种呼吸系统的疾病,其它的科室的同志对此了解不多,治疗上还离不开专业科室的人员,可能只能等疫情过去了。我问,这何时是个头啊,她也是很无奈,不过她说,今天楼下的发热门诊的病人就不多,不象前几天,一天就百十来人,没准儿,天气热了以后,疫情可能会缓解,那时,这里的病人再能转走,他们就可以回家了。说着这些,她的眼里充满着憧憬……
下了夜班后,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睡着,环境太乱了,窗户上由于后勤服务没有跟上,窗帘还没有。迷迷糊糊到了中午,医院的工会给我们每人发来两合蜂王浆,据说可以增强免疫力。我们终于感到心里的一丝安慰,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们医院心脏监护病房(ICU)发现了一名病人感染了SARS,可能又一个病房需要隔离了……
唉,何时才能看到希望,但愿SARS是一种季节性的疾病,天气热了以后能够趋缓,这样给科研人员腾出时间,研究出疫苗来,SARS也就能够战胜了。
5月2日 28℃
今天是早班,8AM~2PM,早上起床后,吃了早点,就去接班了。今天的护士长换了,据说刚从地坛医院回来,隔离措施比较严密。衣服穿得更正规了,今天又有了脖套,穿了隔离衣后,我对镜子一照,身体再没有暴露的地方了,看来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可我还没进隔离区呢,汗就已经下来了。
进了隔离区,查了一圈房,病人还比较平稳,有两个还发着烧,咳嗽得都不太厉害了,昨天,已经都填了转院卡,今天可能随时会有部分病人从我们这里转到胸科医院去。但是,每个病人的治疗还照样需要进行,针对每个病人开好了医嘱和药物,写完了病程,已经近十点了。我已经觉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防护镜上已满是哈气,眼前白芒茫的。由于SARS病房不能开空调,我们都已感到奇热无比,我感到口罩都变得很沉了,呼吸也感到了困难。
我从污染区出来,来的半污染区,准备休息一下,护士叫我,说5床和10床感到难受,要见大夫,没办法,我又重新进到病房,原来是她们听说要转走,不太原意,想要留下。可是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无法再改变了,我只好尽可能地安慰和劝导她们……
病房里面的时间过得奇慢,休息时我只能坐着,不敢乱动,我感到我的汗已经湿透了全身能够吸汗的地方,口罩肯定已经全湿了,湿透的防护服是最可能遭到感染的。我等着通知,准备病人转院……
这是我想,我们的医院的医疗条件还是不足,那些病人病得较轻的,应该可以到院子里散散步,房间里应该有电视以打发无聊的时间,也应该有独立的空调,病人的房间的空气应该持续交换,排出的废气应该经过消毒再排出去,大夫可以通过监视器观察到病房的情况,并通过对讲系统与他们聊聊天……
时间就这么在我的遐想中流逝,2点了,还没有接到转院通知,可能下个班会转吧。我交了班,下到楼下,脱去喉服后,我不尽打了个寒战,里面的衣服全湿了,就想从水里捞上来一样,口罩也沉甸甸的。
换了衣服后会到生活区,看到手机上有10多个未接电话,看来外面有好多关系我的朋友惦记着我,正准备吃饭,手机又响了,是我天津的同学,当得知我已进入非典一线,他一个劲要我保重身体,问我吃得够不够,有没有水果……我告诉他,其实我在这里面,心里踏实多了,虽然我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家人,但我也不用再忧虑回家后把病菌带给他们,感染老人和孩子。
5月3日
今天下午接班,接班后,就得知我们病房收了一个12岁的女孩,是地坛小学的学生,她在家发烧38度已经4天了,没有明显咳嗽,但片子上有些影子,血象不高,但血小板较低,怀疑“非典”,以疑似病人收住入院。
小女孩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戴着口罩,见到护士进屋扫床,她便夺到墙脚,我便问她是否是害怕,她说不是,是怕传染给我们。我不禁鼻子一酸,心想,如果她不是SARS,要是在这里被感染上,那可太怨了。把她单独安排了一个病房,吩咐她不要离开房间,开着窗户,多多通风。本想和她多聊两句,可是外面的护士叫我出去,又要有病人转到小汤上去。我们病房有三个,需要把传染病卡片、病历及治疗方案用传真机把资料传出去。我添好卡片,拿着资料到了一楼,开始一页一页地传,由于传真机比较古老,且又是使用的内线,传真只能每次电话打通后传一张,这样,三份资料传了大约一个小时,汗水早已在喉服内流成了小河,眼镜里也存了一汪水。我的心情有些烦躁,使劲拍打了几下传真机,有给总值班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要把资料给他们送去,他们听了,语调都变了,赶紧说要给我们换台传真机,我带着莫名的快乐,发完了传真(心理可能有点变态了)。
另外,我们的服装也开始出现质量参差不齐,今天的隔离服薄的象自由市场买菜的塑料袋,根本系不住,袋子一用劲就断,衣服一拉就撕。看来,卫生物资的储备可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的质量已经不能完全有所保障了。
这些年,经济发展的确很快,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GDP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卫生工作却没有跟随着前进,卫生的缺口十分庞大,各家医院靠着以药养医维持生计,维持发展。基础卫生事业根本无力发展和提高,各家药厂靠着仿制品来度日,而根本没有真正的科研投资。而医疗卫生的改革,在没有理顺医疗价格体系时,就冒然推向市场,妄图以市场来保障十几亿民众的健康,想把国家医疗保障的负担推入市场,由市场经济来解决。殊不知,市场经济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原则的,而人民的卫生健康的保障体系如果以此为目的,就可能使这一体系出现崩溃的可能。此次疫情的演变,可以说是一次天灾,可能更是一场人祸。由此暴露出基础卫生事业的不足,基础科研人员的缺乏,卫生物资储备的不足,卫生科技投入的不足,基层卫生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国家卫生防疫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且缺乏医学综合素质及应急反应能力。我们虽然错失良机,但我们的新一界领导觉悟得还不算太晚,英名决断,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我想这一定能有所成效的,一定会把SARS的损失控制得最低。我想,这场战役之后,中央也可能会重新考量卫生事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可能会以另一种思路来考虑卫生事业的发展。
5月4日
今天的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由于考虑到下班后,就差不多3点了,回到宿舍可能会影响别人休息,而且自己也休息不好,就和小林换了班,我就一直上到早晨8点,下次他再这么上,这样一个人累点儿,另一个人就能休息好点儿,省得两人都休息不好。
上午都在宿舍里,实在是闷死了,带进来的大富翁6都快打穿了,这日子刚过了5天,离解放还远着呢。中午的饭还是盒饭,旁边的庄大夫实在没兴趣吃了,就啃起了饼干,我说这怎么行。正说着,隔壁传来了歌声,是护士小张过生日,小张推门进来,给了庄大夫一块蛋糕,说庄大夫的爱人给她发短信祝福她了,她要表示感谢,我问,蛋糕是谁送的,她说是她老公送来的,这时候亲情和友情才是最真实的,有些人因为恐惧,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我们了,害怕我们是带菌者,是潜在的传染源。
下午实在憋闷,而且带来的水果也吃光了,洗涤用品也不够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我洗了个澡,穿上自己的衣服,出了医院,医院门口真是肃穆,平时我们医院门口的车位都没有,今天外面空空荡荡,有一种萧条的气氛。上了街,看到熊猫环岛广场上好多人在放风筝,看着天上飞动的风筝,看着街上快乐的人们,看着路边嘻闹的孩童,看着青青的草地,嫩绿的杨柳,我似乎已经忘却北京还有非典的肆虐,似乎忘却医院中还有瘟疫在漫延,我也感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值当的。
下午买了本新闻周刊,这是我平时最爱看的杂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也很想知道一些别的声音。另外还去超市买了些水果和日用品。回到宿舍已经快5点了。听到今天北京的发病人生开始下降,只有69人了,我心里很是高兴,心想有可能真如原先估计的那样,病毒会在天气热的时候得到控制,给科研人员留出些许时间,以便研制出疫苗和诊断试剂,彻底控制SARS,这可能是我们希望所在。可是不好的情况是,内蒙古的数量开始上升,从昨天的10人到今天的35人,这要当心啊,会不会现在内蒙古的气候适合病毒繁殖呢???
5月5日
昨天8点接班,接到通知,今天我们病房要转走3个病人,上了班,先整理他们的病历,需要填的,上个班的刘大夫已经干了,把病人的片子和病历用一个大口袋封好,写上各自的名字,就等通知了。
9:30,通知转病人的车到了,我把他们的病历拿下楼,交给李大夫。在医院的门口,停着一辆120“海狮”型救护车,车上有两名全副武装(当然是防护服装)的120的人员,救护车的前后各有一辆公安牌照的小汽车,还闪着警灯,显出了一种紧张。今天一共应该转5个病人,都是确诊SARS的,而且病情都已经不重了,他们需要转到胸科医院继续观察、治疗,以度过剩下的隔离期。这时,我们病房的张先生和老两口互相搀扶着走到车前,他们都戴着口罩,在上车的一刹那,他们回过身来,向我们挥了挥手,表示对我们的感谢。看到他们蹒跚消失在车中的身影,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次疾病呈现出簇发性,得病的人大多是一家的或是一个单位或学校的,一家一家的病人,在隔离的时候,如果确诊,我们都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这样,既使得病,也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时刻,不能说不是一种安慰。我想,如果我的家人得病,我一定要陪在她的身边,哪怕就此告别人世,但如果病的是自己,又多么希望不要把病传给家人。
10:15了,4床的病人还是不肯转院,她以各种理由拒绝转院,没办法,主任又上去劝说,仍然无效,只好先转4个了,陈主任挥手准备发车,但120的同志拿着一张纸,说卫生局35号文件命令转病人时,转出医院必须排大夫跟车,但救护车上又没有给我们准备位子,我们的大夫只好与病人挤在后面的车厢中,虽然穿着防护服,但要在这么狭小的空间中颠簸1个多小说,那也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的大夫毫无怨言,李大夫还与朱主任争着要去。我们在一边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让陈主任请示院长,看是否能和其它医院一样,派一辆车跟着。但是,医院没有任何表示……警笛响起,救护车瞬间就消失了,祝这些病人早日康复,祝李大夫一路平安,千万别染上SARS。
12:10,发烧门诊报告,说有四个病人,单位拿了支票来住院,原来他们是一个工地上的工人,住一个房间,其中一个三天前发热去医院看病,医院没有确诊,且自己也没有重视,也不愿花钱留观(现在的政策是确诊SARS的,政府可以负担费用,但疑似的如果单位不负担医疗费用,就可能自己掏钱了,政府为什么不索性再大方一些,这样所花费的成本未必就会很大),结果回去后同屋的另外的两个同志也不幸发烧了。检查的结果,其中两个肺上有阴影,另外两个还没事,先以疑似病人收下,留观,填卡,开医嘱,忙到2:10,总算可以休息一会了,最里面的隔离服、裤子全都湿透了,休息吧,但愿后半夜没事。
5月6日
今天由于倒了个班,休息一天,早晨醒来,感到嗓子有些干,身上不太舒服,赶紧量了一下体温,还好36.4℃,没事,可能是睡觉有点着凉,我和同屋的庄大夫一说,他乐了,说我们现在都神经了,昨天他也感到有些冷,也害怕得了非典,后来量了体温才放心。我们虽说不害怕,但是内心里还是有些惴惴然,就连自己科里也害怕我们回去,会把病毒带回去。
今天,接到我妹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问北京的情况,她说,看到我传去的照片,说我们的口罩简直和尿布差不多,我说那还不至于,口罩也是每天清洗和消毒的,就是显得旧点儿,而且中国目前的条件就是如此,很多的物资还很紧缺,她说就是现在,美国的N95型口罩也断货了,3M每天生产的口罩都运往了中国。在美国,很多的中国同胞都想在这个时候为国家出点力,但是能够接收捐款的部门只有中国慈善总会,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愿意直接把捐赠用于临床一线人员。我对她说,临床的防护用品目前还是充足的,更需要的是改善隔离区中的医护人员环境的物品,象电扇、手机(由于隔离需要很长时间,医护人员需要与家人联系)以及传真机等,另外就是新鲜的水果、维生素等。还有就是改善病人环境的物品如收音机、电视以及和用来和家人联系的手机等,病人在隔离区中不仅生理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心理上还忍受着孤独寂寞煎熬,由于他们是恶性传染病患者,作为医护人员,原则上是尽可能少的与病人接触,但是反过来,病人这时更需要关怀,需要与人交流,这样才不至于产生心理障碍,因此,在隔离病房中应该有电视,有电话,有收音机等物品,是他们心理上能得到舒缓,他们更需要听到音乐、看到电视、打电话与家人倾诉。
今天,接到去支援非典定点医院——胸科医院的护士小张打来的电话,说那里的条件更差,病房是用保温板盖起来的,都有空调。病房外面的地面还是土地,而且病人房间的窗户是对着通道的,我个人认为这不合理,安理,这种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的病房,病人的房间的窗户应该背着通道,通道中有观察窗和门,便于医护人员使用,而且能够相对保护医护人员不被传染。我问了他们防护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防护还是不错的,但口罩也是回收重复使用的。他们住的是一座被征用的宾馆,住的条件比我们好有电视,电话,两人一间,但就是驻地距离医院较远,需要45分钟的车程,医院没有洗澡的地方,需要到驻地才能洗澡,好在他们就2周,已经过了一半了。
今天晚饭的时候,看了卫生部通报,北京确诊的为70人,已经是第三天在两位数了,真希望,天气再热些,赶紧到36℃,从网上看到这种病毒在36.9℃就会死亡,不管我们如何受罪,但愿我们一个月解放时一切都能恢复正常吧!
5月7日
今天是上午班,8:00到下午2点,班已经上了一周多了,对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一点适应了,每次穿了隔离衣防护服后就开始出汗,大概一两个小时后,汗就出光了,也就适应了。反正活儿是必须去干,这就是所谓的专业精神,任何一个医护人员都必须执行的专业操守,这不分是不是党员。
今天我们病房一共是8个病人,上午主任查房,结果其中7个都确诊了SARS,主任要求其中4个将转走,4床准备明天出院,她在我们医院已经住了一个月了,病已经完全好了,体温完全正常,肺部的阴影已经完全消失,血象已经完全正常了,这一切已经持续了8天,今天决定让她明日出院,这也将是我们第一个SARS病愈出院的病人,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别看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她高兴得直要拉我们的手,我们也为她高兴,告诉她回家后多注意身体,再休息一周后再去上班。谈到这个病人,刘大夫说,是她四月初收的,当时和她一批来的7个病人,有两个死了,另外的转到地坛医院去了,她比较轻,而且死活不愿意转院,没办法只能留在我们医院治疗,目前看,效果还不错。
接着,刘大夫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她的女儿。她已经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了,她和我们不一样,由于我们是综合医院,没有传染科,SARS病人的治疗主要归呼吸科,因此,呼吸科的大夫就成为了SARS病房的主力,我们可以轮班休息,他们却要长期坚守,还有一部分呼吸科的大夫需要支援胸科医院,他们的人员也十分紧张,许多大夫在一线已经干了超过一个月了,而且一开始的防护,由于北京市实行内紧外松的原则,没有现在完备,但是他们还是十分重视,自己主动与家人隔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家人了。刘大夫说,昨天,她实在忍不住,就到她妈家楼下,打电话给她爸,她爸让她三岁的女儿在十三层楼上向她招招手,她什么也没看清,只看到她闺女穿着她去年买的黄色的小背心……说到着,她停住了,我看到她眼罩里有了很多水……
今天又收了四个病人,其中一个较重,发烧38.5℃,肺部又阴影,另外的几个就只是发烧。近来,非典的病人的情况好象以轻症的比较多,而且我们医院已经好久没有听说有医护人员出现感染的了,这似乎表明,非典在逐渐得到控制,可以预测SRAS疫情将随着天气转暖,逐渐得到控制,但不会绝迹,疾病会呈散发的形式出现,市民仍要注意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对在治病例和散发病例要做得严格的消毒隔离。SARS疫情极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再度出现爆发。对于科研部门来讲,抓紧这宝贵的半年的时间,研究出确诊手段及防病措施(包括疫苗)。对于下半年,我国要主要预防SARS在西北部各省的蔓延和传播,由于那里的气候将开始有利于病毒的生存及疾病的传播,且那里的医疗水平比起北京、广东要差得多,而且大部分是农业省,将迎来农民返乡收割的情况,这要比北京抗击非典的难度要大得多的多。
5月8日
我们楼上的病房现在有7个病人,6个还没有确诊,一个已经确诊,是个76岁的老先生,是原警察学院的教授,为人很是开朗,对于自己得了这个病,并不是十分在意,他总是很乐观,每天都要打电话安慰家中的老伴。今天,按照上级的规定,他要转到温泉的胸科医院去,他仔细问了问我情况,害怕是否自己的病又加重了,才要转走,我告诉他,以后确诊的SARS病人都要转到定点医院治疗,而不是因为病情加重了,他这才放心,又问我胸科医院的情况,我告诉他,胸科医院的病房条件比这里好,每间病房都有卫生间,而且安了电视,空调。他放心了,并给老伴打电话,首先安慰了老伴,又把要转院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告诉我。他家在裕中里,由于楼里有人得病,他不知什么原因也传上了,已经病了10多天了,现在比较稳定。他还谢了谢我,并要我等疫情过去后到他家去玩。我心头一热,这是到SARS病房中第一个对我说这样话的病人,而且,我也感到对这个病已不再那么恐惧了,它是能被战胜的。
转院的手续很罗嗦,需要填传染病卡、转院病历、治疗情况表,然后还要传真出去,并复印全部的病历。来到一楼,去发传真,碰到了娟娟,她是去年刚毕业的一届新同志,本来按规定,他们是不需要在一线工作的,由于她在SARS爆发时正好轮转到急诊,只好留在SARS病房工作,她已经毫无怨言地在这里工作了近一个月,而她的同伴们都在外面。我曾问她,在这里害不害怕,她说,咳,谁让咱们干上这个的,注意防护就可以了,就是这身衣服太捂了。
今天下了班,看到手机上,22个未接电话,其中三个是外地的病人打来的,我回过电话去,原来,他们知道了我到一线工作,都很担心,嘘寒问暖了一番,并再三让我保重,注意安全。我真是很感动,我头一次感到了作为一个大夫的自豪,也这才感到医生和病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而我们以前,在媒体上总是把医生与病人对立起来,好象他们就是买卖关系,病人是单纯拿钱到医院消费的,而医院收了钱就要提供服务。难道医患真是这么单纯吗?其实,医生和患者是一体的,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疾病。其实,中国的医疗价格是扭曲的,病人花的钱大部分用来购买药品和消耗品,而为医疗行为的付出仅几圆到几十圆。中国医生的收入据统计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名,仅排在北朝鲜之后。在这次病疫面前,医生和病人终于站到了一起,共同面对非典,一起战胜非典。
5月9日
写这段日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10号的凌晨了,我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快三点了,由于洗了澡,比较精神,也觉得肚子有些饿,就拿起凳子上还没吃的夜宵,一摸,是凉的,看着庄大夫已经睡熟了,我蹑手蹑脚地拿着夜宵到楼道里,想到九楼好象安了微波炉,于是便爬到九楼,把夜宵放到微波炉中热了一下,便在九楼的楼道里,打开电视(九楼昨天安了一台背投彩电),看了看夜间的新闻报道,北京的疾病好象有所控制,确诊人数只有不到50人,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心想,但愿这场病疫能够早些结束。吃完了夜宵,感到饱了,便回到床上,准备睡觉,可是,不知怎么,就怎么也睡不着,但我不准备吃安眠药,因为吃以后,第二天总是不舒服。
想一想今天,这个夜班还挺忙,刚上班,就转走了确诊的病人,看着他们被120车转走,我感到了些许安慰,现在急救车前后不再有警车“押运”了,而且医院也开始出车,帮助跟车的医生可以坐医院的车,避免交叉传染。今天总值班二线大夫是呼吸科的高大夫,他已经在非典一线战斗了快一个月了,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批支援地坛医院的医生,在那边干了10天以后,由于本院的非典病区开了以后,缺少具备呼吸科专业的医生,所以又把他从地坛医院抽调回来(本院有部分呼吸科大夫还要支援北京胸科医院的非典定点医院)。高大夫总是事必躬亲,每个病人都要亲自去检查,今天他还举着他的脚让我们看,他脚上的五层鞋套都磨破了。
今天的夜班我们楼上的病房收了4个病人,其中三个已经能够基本诊断是SARS了,而且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今天的病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而且都不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接触史,不能确定传染途径。另外,在他们周围并没有隔离,出现了来源不明的散发病例,这将是十分危险的,如果SARS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爆发,那么,控制起来的难度将加大,而且会随着民工返乡期的临近,可能会把这一病疫带到中国广博的农村中去,那可能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后果,但愿我这只是杞人忧天吧,真希望天佑华夏。快4点了,还是睡吧,但愿是一个好梦。
5月10日
按照上面的安排,我们要工作到这个月底,看来我们已经有盼头了,今天已经是十号了,也就是说,非典的战斗征程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一了。今天的班要到凌晨两点才上,白天没有什么事,想干点事,可是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昨晚没有睡好,白天睡觉总是半梦半醒,我睡觉还有个习惯就是房间要很暗,怎么让我白天睡觉,可真是受罪。
今天知道昨天报的非典的感染人数已经大大下降,全国只有118名,北京只有48名,但愿,一切都是真的,北京能够在这个月,把发病人数控制到一位数,这样我们也没有白受罪,而且如果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转院机制,也就是确诊或疑似SARS的就马上转到定点的医院去,那样,我们医院就可以逐渐地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下午,老婆给我打电话,说在我们医院楼下,说给我们把他们公司以往的北京青年报拿了一些来,让我们可以带到病区去,以便能够缓解在病区中的单调时间,我接到电话,下楼后,看到她在汽车边上,拿着两包东西,我让她把东西放在马路边上,尽快离开,可她总却磨磨蹭蹭,说还要给我买水果,我无奈,只好让她把钱也放下,这才打发她离开,我知道她怎么想的,我们结婚后,象这样长的时间不在一起的情况还很少,但是,医院附近还是很“危险”的,而且我也是一个危险分子,谁知道是不是已经感染了SARS,现在还是潜伏期呢?
看了带了的东西,有两包巧克力,是送给我们同事一起分享的,报纸虽然是就的,但总比没有强,可以带到病区,如果不忙,可以打发一下时间。今天晚上就可以带了去。
5月11日
今天凌晨接班比较早,本该2点接班,我12点半就去了,因为在宿舍里也睡不着,老想着接班,怕误了时间。接班的时候,正好雨刚停,月亮露出了头,天空中似乎还能看到云,空气很是清新,肯定没有SARS病毒,如果能够在雨后的静夜中散散步将是很美妙的一件事。
上班又要穿上隔离服、防护服、再穿隔离服,不知套了几层鞋套,带了几层手套、反正,把自己所有暴露的地方都捂上了以后,我又进到了病区,和刘大夫换了班,让他回去休息。他告诉我,我们楼上今天都收满了,这也就是说,今天夜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夜里将没有什么事,我可以稍微休息休息了,还好我拿了报纸,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早上8点下班,回到宿舍后,吃了早点,上了上网,看到温家宝去了山西检查工作,并说要防止做表面文章,看来中央对非典感染人数明显下降也是有所担忧的,的确,如果再出现漏报、瞒报的情况,局面将无法收拾。
但是从昨天的情况看,发病人数确实是在下降,我们发热门诊昨天夜班才看了五个病人,只有一个疑似的病人收入院了,这与我们刚开始时的一个班看39多个,一天要看100多人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非典的疫情从我们这里来看,的确是得到了控制。
今天好象是母亲节,也没有机会去家里看看妈妈了,老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要是她知道了,还不得天天挂念着,血压没准儿又该控制不住了,我现在还是一直骗她,说自己怕把病菌带回去,就住在租的房子,不回家,就这样,老太太还两三天一个电话。说实在的,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别得病,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母亲节,愿妈妈节日身体健康!
5月12日
今天真的很高兴,真的高兴。今天早上一接班,刘双主任查房,经过几次检查,2床、4床和18床可以排除SARS,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出院了,其中,2床和4床是上呼吸道感染,而18床则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现在他们都已经痊愈了,总算可以解脱了。虽然,我要干的事很多,可是我还是很乐意,SARS我希望是越少越好,哪怕是疑似的,也是越少越好。给他们分别办好了出院手续,开了要带的药,并且还要给他们写一个诊断证明,其中着重要写的是除外SARS!这样他们就再不会胆战心惊的过日子了,他们周围的人们也就踏实了。另外,我们还要分别每人填两份传染病登记卡,分别发传真出去,以便疾病控制中心随时掌握信息,以保证每日公布的数据的准确性。
这样,我们四楼的病房就剩5名病人了,护士的压力也少多了。就在下午一点钟,我又接到通知,由于我们医院的病人已经减少,准备把三楼和四楼的病人都合并到三楼的病房里去,我又准备病历,并写了病程,我们楼上的剩下的五个病人,情况都还稳定,只有一个血象不正常,另外的就是胸片不太好,他们转到楼下,每人一间病房,楼下的病房窗户比较大,空气流通要比我们楼上好,这样也有利于他们恢复吧。
虽然这个班,我基本足足实实干了6个小说,但我心里还是愉快的,我们病房的病人都清空了,我临走时,接到通知,让我们这一组的同志在宿舍待命,如果没有新收病人,就随时听班。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即将结束了。
今天晚上的疫情统计出来后,北京的确诊人数只有48名,其中只有9名是新发病例,看来我们真的要胜了,如果发病人数降下来了的话,我们医院的SARS隔离区也就可以完成使命了,也可以恢复正常的医疗工作执绪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将要完成了。听说,北京友谊医院的发烧门诊已经撤了,可能我们这里也快了。如果这样,我们日记也就该结束了,有很多的东西本想都一一记录下来,由于精力不继,文笔拙劣,都没有记录下来,也很遗憾。
晚上,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在北医急诊科上班的时候感染了SARS,两周前转到小汤山医院去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随即给我们那位女同学打电话,但是手机没开,但愿,祝她GOOD
LUCK.
5月14日
昨天没有记日记,本以为就这样,疫情就会控制下去,我们也就可以就此休息了,可是今天早晨还是接到命令,晚上8电还要去接班,四楼的病房还要接收病人。
刚才上网,看到了北京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因感染SARS,因工殉职。看着看着,我感到眼睛发酸,又想流泪了,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冷血的人,已经很少有事情能够让我感动,但是这次抗击SARS的工作开始以来,我总是有一种要哭的感觉,是SARS疫情太严重了?是压力太大了?还是身边的事情太感人了?
丁秀兰的牺牲,的确有很多感人的地方,但这一切似乎又是可以挽回的,又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的工作由于在一开始的失误,造成了我们大多数医务人员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上的模糊,防护的不重视,造成了很多例的院内感染。甚至我们医务界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人不十分重视个人防护,认为自己的抵抗力天下第一,以前很少得病,这次肯定没有问题,这种人以老同志居多,因为他们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几次疾病的流行。另一种人对此恐惧异常,生怕平时吸入的空气中都有病毒存在,在医院的工作中畏首畏尾,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这种人以20多岁的年轻同志多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对此产生恐惧也是情有可原的。
丁秀兰主任,从文章上推测应该是4月14日去急诊监护病房看6名发着高烧的急诊科护士时感染上的SARS,但是早在3月3月24日,北京市卫生局就已经就SARS疫情在医院内部做了疫情通报,并报告已有2名患者死亡。但是这样的通报没有引起医护人员的足够重视,当时就连我们也没有重视,只是建议使用干扰素点鼻。而且当时北京对此疫情在北京的传播采取的是隐瞒的措施,所以这个在中国广东、香港等地蔓延的疾病并没有引起北京医务人员的足够重视,甚至他们不知道这种疾病的诊断方法和预防措施,这也是造成丁秀兰主任被感染的原因所在。如果当时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严格的,象现在一样的SARS疾病的诊断隔离措施;如果人民医院能够早点采取对SARS疾病的防护,早点对发病的人员进行有效的隔离;如果丁秀兰主任对此病有正确的了解,意识到6名高烧的护士有可能就是SARS患者,对自己采取必要的防护;那么丁秀兰主任就可能不会感染SARS了,可能人民医院也不会成为重灾区,北京也不会重蹈广东、香港的复辙。
丁秀兰主任的治疗又有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早在今年4月1号、2号分别有报道香港、新加坡使用康复病人血清治疗重症病患的消息,而其后4月21日的北京302医院的姜素椿教授使用血清的成功经验,但是自4月22日丁秀兰主任转到北京地坛医院以后,竟然没有人提到使用血清治疗的手段,直到其最后全身多脏器衰竭后方想到用此方法,尽管有很多的“专家、教授”,但也没有能够挽救自己战友的生命。疾病的治疗贵在“尽快,尽早”,按照姜教授的观点,就是:“要在感染非典病毒早期,科学、合理地使用血清,尽快,尽早”。疾病的预防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能够做得“尽快,尽早”,北京也不会这样了,全国也不会这样了。
一个老百姓的错误损失的可能是他的生命,一个医生的错误损失的可能是他的病人的生命,一个部门领导的错误将可能损失的将是所辖部门的生命,而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将损失全国的生命。
5 月15日
今天的班要到凌晨2点才上,白天没有事,很是无聊,本来准备回科里拿本书,但由于我们已经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别人害怕我们身上带有SARS病毒,对我们都敬而远之),我只好作罢。同时,我在网上看到有些SARS康复者受到单位、邻居甚至家人歧视的报道,的确,由于人们对这种病的了解还不十分充分,造成对SARS有一种恐慌的心理,对病人的惧怕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因此要多多把实际的情况告诉民众,让人们消除恐惧心理。但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就从人们对病毒性肝炎的恐惧,就可以猜到对SARS的恐惧情况。肝炎经过多年的研究,可以说对之了解已经很深刻了,但仍有许多人对之恐惧有加,更不要说SARS目前了解得还不充分了。
今天听说8病房的一个病人,因疑似SARS而转到SARS病区的观察室,主要的症状是高热、血象高、肺部有阴影,而且病人两个礼拜前从香港过来,是来做手术的,手术在一周前已经完成。8病房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害怕,把自己隔离起来,住到了我们的外科大楼的隔离生活区。看来SARS已经有蔓延的趋势了。÷
后来,我们庄大夫从观察室下班回来,告诉我8病房的病人的情况不象非典,他们也有点草木皆兵了,的确,非典的诊断到目前还是以临床的症状和一些常规检查来诊断,说实话,还没有可以确诊的手段(传染病的确诊,我认为就必须可以能够证明存在有病原体感染,就非典而言,就是能够证明有冠状病毒感染)。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也是造成临床和实际工作中恐慌的原因之一。
5月16日
呼吸科的病房经过改造以后,病房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里面的护士站也改成了病房,原来的两个人的房间全被隔成了一个人的小房间,这样整个四楼的病房就从原来可以收8个病人的规模扩大到能够同时接收18人。外面的办公室也缩小到只有一间了,护士大夫共用,没有休息的地方了。
说实话,这一夜还真清静,一晚上没事,可是这六小时(2am~8am)比我以前的任何一个班都累,完完全全穿着防护服,整晚没有合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而且还要忍受着消毒水的味道和弥散在空气中的消毒机产生的臭氧,别提多难受了,下了班,人整个昏昏沉沉,没有一点食欲。这一整天都是这样,直到睡觉。
5月17日
昨天一天都昏昏沉沉,睡了一觉总算是缓过来了,早上7点吃了早点,就去接班。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很好,蔚蓝的天空上淡淡的几缕白云很是精神,已经好几天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我的精神也随之一振,可能这又是一个好兆头。
早上,我老婆发短信来,说带孩子去八大处,今天天气不错,他们一定会玩得很好。我的班估计今天也不会有太多故事。上了班,还是现查房,看了一圈病人,有一个小伙子可能因为对药物过敏,背上有些皮疹,比较痒,我把他的点滴和口服抗菌素停了,改吃点中成药,并开了点抗过敏药。另外的病人都按要求开了点滴,并需要复查血常规、胸片,以便进一步诊断。
后来,复查的结果,有三个病人的血常规都显示白细胞偏低、而且血小板也低,这不是一个好现象,非典的患者有一个指标就是这样。另外使用病毒唑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现在好在三个病人的体温都不高,那只好现把病毒唑停了,观察观察再说。开了医嘱、写了病程,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令外的活儿就是定期的消毒办公室,就是在1000ml的喷壶里加8片键之素的药,然后溶化后,喷洒地面。就这样干耗着,到了下午,快一点了,SARS指挥办得到病人的胸片结果,告诉我,三个病人的结果没有问题,都由疑似改成临床观察(这是北京SARS疾病控制中心于昨天推出的新名词)。我又得另外填写一份更正表传给指挥部。忙完后,指挥中心又说要把我们四楼和二楼的病人合并到四楼来,看来病人已经渐渐少了,而且原来二楼我们本院的几个确诊SARS的同事已经转到中日友好医院去了。病房合并了以后,已经是两点多了,我可以下班了。
三点钟到了宿舍,我才吃上中午饭,可能由于是周末,今天的饭不怎么样,不过我是饿了,也就不管许多了,三下两下就吃完了,然后上网看了看,看到一家新加坡媒体报告日本支援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认为北京的疫情可能被夸大了10%,他认为由于目前SARS的诊断是所谓临床定义诊断(即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来诊断他是不是SARS),这样就有10%的误诊的可能,造成所谓过度诊断。但是我认为,在我国,过度诊断要比诊断不足强,这样可能更有利于遏制这一疾病在我国的蔓延吧,而且好象我国大陆的诊断标准比WHO的要宽泛,比香港就更松了,这可能也是政府的一种策略吧。
5月18日
早上一起来,就觉得浑身酸软,咽部还有点发干,好象有点流感的前趋症状,赶紧试了试表,还好,体温正常,也许是昨晚没睡好。得,昨晚洗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呢,赶紧去拿,还不错,衣服道是洗干净了,昨晚就为这洗衣机,折腾了半天,这洗衣机是医院配的,是海尔的滚桶洗衣机,可以是要以水位来控制洗涤程序,原来我们把排水管直接插到地漏中,结果白白放了一小时的水,洗衣机愣是没有启动,一小时后我一看,衣服还是干的,后来琢磨半天,把排水管抬起来后,洗衣机才开始正常运转,咳敢情是上排水的,水位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行。这样折腾了半天已经是午夜12点了。
今天上班,到了班上,我们病房已经是11个病人了,后来大概是3点左右,又收了2个也是××彩管厂的(之所以在这里把名字隐去,是因为现在好象出了一条法律,是所谓传播谣言罪,我害怕到时候别因为写了这个,被判有罪,可是冤枉),这样就已经全收满了,××彩管厂的病人已经达到8人,按上面的要求,都诊断为医学观察,我给一个叫张峰的病人的屋里装了一台电扇,同时问了问他们厂的情况,他说,他们厂昨天已经停产了,有一个工人已经诊断为SARS,停产一天的损伤可能要有一个亿呢。
网上有关今天的发病人数已经是很低了,全国只有新增28人,北京17人,而北京新增的疑似病例只有32人。而当晚我们医院又收了12个病人,都以医学观察收到了病房,由于4楼的病房已经收满,本来准备关闭的二楼的病房又重新开放,我们休息的可能性也彻底泡汤了(原准备二楼四楼合并,二楼的大夫来四楼上班,我们先休息5天)。这样的情况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5月19日
说实话,这样的工作真是没劲,诊断要根据卫生部的标准,还要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诊断,上面说是确诊,就确诊,说疑似就疑似,当然上面的大夫也会看看片子,问问检查结果。现在又有了个医学观察,也就医学观察,疑似的病例也就少了。治疗完全系统化,有固定格式,也就那几种药,就是病毒唑、左氧氟沙星、穿唬宁,再就是强的松龙和胸腺肽。确切的治疗药物也没有,主要还是对症治疗、预防合并感染,再就是等待病人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了。
我个人体会,当然也是从各种报道中了解了一些浮浅的东东,这个病的诊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手段。首先,各位大师对这种病的病原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目前所说的冠状病毒,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另外,就是既使是认定冠状病毒感染,冠状病毒的检测手段还是没有,既使现在各家都在宣的酶联免疫法,也没有经过鉴定,咱们大陆的新闻报道总是正面的、积极的,既使是非常负面的消息也总能挖掘出积极的一面,这就是所谓辩证法。目前,SARS病毒的检测方法,其实就是针对冠状病毒的检测,主要有德国ARTUS公司的荧光定量PCR法、和美国CombiMatrix公司DNA芯片检测法,这两者诊断早、灵敏度高、但成本高。另外,就是大陆的几家科研单位的,一个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间接免疫荧光法、冠状病毒IgM/IgG抗体特异性酶联免疫法,这两种方法的成本低,但不适合早期诊断,还有就是北京大学的RT-Nest
PCR检测法,但还没有经过鉴定。现在在北京大部分的临床诊断中,还没有应用任何的病毒检测,也就是说,卫生部的诊断标准仍以临床的表现为主要的诊断标准,而且现在绝大多数的医院也采用这种诊断方法,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漏诊和误诊。
治疗上面,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SARS的发病机理,以及病理生理变化,对于为什么出现一些病人严重的呼吸衰竭的原因没有确切的证明。目前的治疗包括抗病毒的药物的选择,在香港和加拿大都认为病毒唑已然无效,而且毒副作用大,已经废弃使用这种药物,但在北京仍被大多数医院采用。另外,血清的使用,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才用,但在北京仍然很少使用,而且使用的时机也不恰当,贻误治疗时机。激素的使用上面,这在香港和加拿大后来的治疗中以短程大剂量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在我们临床中,还采用着保守的小剂量、长程的治疗方案,我个人认为,小剂量的长程的治疗可能只能降低病人的免疫能力,而不足以抑制病人的过度免疫,抑制肺间质水肿渗出。激素还是应该在使用抗病毒药物后,采取足量、短程、冲击治疗为好,这样可能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
今天夜里值班,××彩管厂又来了6个病人,我们医院的SARS病区全收满了,另外,一个叫赵朋(化名),正发高烧,给予对症治疗、另外按照上面的要求,给予激素治疗。
5月23日
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写日记了,由于21号凌晨的夜班,造成这两天睡眠不足,常常犯困,所以也就没有心思写日记了,整天想的就是睡觉。21号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深夜的班还算消停,没什么事,因为穿着防护服,也没法睡觉,而且天气还比较热,一夜很是难受。
22号一天都没有缓过来,而且又是白班,事情较多,临到下班,又要办一个出院,很是麻烦。不过掐指算来,已经三个多星期了,工作即将结束,打电话给医务处,于处说一定保证按时结束我们的工作。好在也还剩不多的时间了,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了,心理还是感到有一些慰藉。昨天晚上,下班后,听到××彩管厂的病人都被安排出院了,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出院的一共是15个病人,都被排除了SARS,虽然最终的诊断各式各样,但都排除了隐患,可能××彩管厂也可以很快开工,这样损伤就不会太大了。而且也由于他们的出院,我们SARS病区进行了整和,2楼和4楼又按原来的计划合并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休息两三天了,这不,我今天休息,也就有时间写日记了。
其实,现在发热的病人就诊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当病人因为发热来的医院看病时,需要到医院指定的发热门诊就诊,经过量体温、查血常规、照胸片、问病史后,如果没有明确的接触史、胸片、血常规又没有什么特别,就开一些药回家治疗,如果有一项不正常,就可能留观,现在称为医学观察,并且要向疾病控制中心报传染病卡。医学观察期间,病人是一人一间病房,每天接收必要的治疗和检查,如果经过治疗2~5天后,体温正常了,而且胸片及血常规化验也正常,病人又没有明确的SARS接触史,病人就可以出院了,出院时要在其诊断证明上写明排除SARS,并要求在家隔离休息一周,而且还要向疾病控制中心另外再发一个传染病卡,报告病人出院了。如果病人在观察期间或入院时血常规中白细胞低于正常、血小板也低或者有胸片的问题,就有可能诊断为疑似SARS,并要报传染病卡片,病人要住到SARS疑似病房中,这也是一人一间的,在那里给予抗炎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复查,有部分经治疗好转,可能仅有血常规或胸片不正常,治疗后检查完全正常一周后,就可以排除SARS,出院了,出院诊断上同样要注明排除SARS,在家隔离休息一周。但如果病人有明确的SARS接触史、或来自于疫区,发热、而且胸片、血常规不正常,就可能是诊断为SARS,原来将住到我们医院的SARS病房,现在就可能转到非典的定点医院去了。
现在有些病人发热了,不敢来医院治疗,其实,现在医院的隔离防护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而且大家对这个病都比较重视,你没看,现在就再没有出现象人民医院和302医院那样的情况吗。昨天发热门诊看了大约60个病人,最后需要留观的只有2人,发热确实没有原来那样可怕了,但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我个人认为非典在今年的年底或明年年初可能还会爆发,这个非典幽灵,虽然现在用我们的力量建立了一道防护的堤坝,但只有在人类掌握了疫苗之后才能彻底消失。
到我下班的时候,赵朋经过两天激素治疗后,已经退烧了,今天已经把激素停了,病人的情况开始好转了。
5月24日
这一天我休息,也就没什么可以写的了,接到通知,说要给我们打麻疹疫苗,天晓得,这帮××彩管厂的工人怎么就得了麻疹,也不知道是怎么诊断的,他们没一个人出疹子,看来我的传染病需要重新学习了。可能成人的麻疹不出疹子吧。好在我小时候得过麻疹。疫苗就免了吧。和一起的同事聊起这件事,大家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5月25日
由于病房合并,我们今天还是待命,一早就听到昨天我们病房收了一个老太太,晚上就不行了,经过抢救,也没能救过来,今天早晨已经去世了,而且昨晚上班的大夫和护士都要求隔离。确切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两天,没事儿,在网上和一些正式出版的刊物上看了很多反应SARS文章,从中我也觉得很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SARS的反思
SARS的发生可以说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被发现的,当时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一疾病,而且似乎当时的传染力没有后来强。直到今年的1、2月份,出现河源市人民医院大面积的医护人员感染,才使得临床医生开始重视这一疾病,并开始有所防护,但防护并没有象现在这样到位,但这也保护了广东的部分参与治疗的医生。但到2月10号广东仍出现305名感染者,其中105名是医务人员。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对这种疫情的正式的发布,而且其后在广东、海南等地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的抢购风,和广东等地的消毒隔离措施,并且2月18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洪涛院士发布非典型肺炎致病病原体是衣原体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遭到广东的一线医疗人员的广泛反对,但最终被决策层采纳。
2月21日广州市副市长陈传誉强调非典并未完全遏制,要求层层落实,做好防控。这之后,中国大陆的媒体和政府对这一事件出现了令人无法致信的静默期。而香港、新加坡等地却陆陆续续地出现类似病例而且越来越多,并从一开始可以追溯源头到后来无法准确知道发病源头,同时越南、泰国、加拿大等地也相继爆发。
3月5日全国十届人大如期召开,3月18日顺利闭幕。而到3月21日,香港感染人数已增加到165人,北京、广东仍然对此讳莫如深。在3月24日,北京市卫生局下文传达非典疫情,并仍然要求内紧外松。并且在26日的通报会上说仅收治8名输入性非典患者。而广东省卫生厅终于在26日透露该省非典型肺炎的最新数字,截至2月底,广东证实的非典型肺炎个案达792宗,造成31人死亡,单是广州已有24人死亡。
到4月2日,中国官方仍不承认隐瞒数字。4月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宣称北京的沙斯数据为“患者12例,死亡3例”。4月4日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由于不相信这一说法,并在得到一些真实情况后,屹然写了揭发信寄给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视台。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他署名的揭发信。4月11日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教授公开反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说法。
4月20日,盖子终于被揭开了,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分别因为措施不力,被免职。并且由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发布了第一次疫情通报: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山西108例……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SARS疫情的防疫工作才开始逐渐地走向正轨。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些知道这种病的危害,就可能在河源市和广州市进行隔离,那样就可能不会出现以后的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疫情的爆发;如果能在2月初就象现在一样广泛宣传,注意群防群治,那样就可能不会出现这样大面积的感染;如果没有2、3月份的那种难以致信的静默,增加医院间的信息交流、就可能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医务人员的感染和牺牲。
现在,有部分非典的病愈者遭到别人的歧视、甚至部分非典患者可能因为情绪的焦躁,有些过激的行为而遭到媒体的谴责,有些患者或康复者由于给地方带来了疾病,造成部分官员因此下台,而遭当地群众或政府的排挤,所有这一切,似乎不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的表现吧?
政府你有没有想过,正是由于你的失职,隐瞒疫情,粉饰太平,造成民众疏忽大意,隔离防治措施不力,造成瘟疫大面积流行,造成一个个家庭妻离子散(非典患者,他们承受着疾病的打击,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承受着孤独寂寞的煎熬,他们承受的太多了,脆弱的神经就要崩溃了);媒体你有没有想过,正是由于你丧失了透明,一致的静默,而使公众无法得到准确的信息,丢失了保护自己的良好时机;咱们的同胞有没有想过,那些患者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战胜非典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关怀,给他们力量,敞开胸怀,欢迎他们康复归来。
5月26日
今天仍然待命,门诊的病人确实开始减少了,合并后的病房没有再出现爆满的情况,疾病可能真的控制住了。
5月27日
今天是我们支援SARS疫区工作的最后一天,但是听说隔壁的护士们已经接到通知,今天去体检,明天一早将去郊区的定点招待所集体修养,而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同屋的庄大夫有点茫然,便去给医务处和院办打电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仍然听通知,可能这一批没有名额,得等6月3号下一批去修养,而且必须得去,方能解除隔离。我们看来又要在这里闷一个礼拜了,庄大夫打了一统电话后,没好气的讲。
今天中午吃的是烤鸭,每人一份,这是我们进入SARS疫区以后最好的一顿饭了,大师傅还发到了每个人手里,鸭子是我们医院自己烤的,皮很厚,但我们觉得非常好吃,这在平时,食堂买是每份十块钱。看来任务结束了,这算是慰劳慰劳吧。
下午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医院的人通知我们明天一早体检,下午就撤出,去集体休养,具体去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搞得还很神秘。
总算踏实了,休养完了,就可以回家了,总算可以回家了。我似乎也有一种大病将愈的感觉,好象我也得了SARS?
不是尾声的尾声
一个月了,这篇工作日记就要在此结束了,我其实不爱记日记,记得小时候还曾为不记日记,和妈妈吵过架,还被爸爸教训过。但是自从得到消息,要进入SARS疫区工作,我就有了记日记的冲动,SARS的疫情虽然不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流行病灾难,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场流行病爆发。我自从开始卫生工作以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会有如此大的风险,既使是战争,军医也是在第二线的,死亡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离我们这样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医生,还有如此大的风险;没有想到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疾病,我们医疗工作者竟然束手无策。
本想能够很好地记录一下医生和护士抢救病人的镜头,但由于上班后的工作实在太多,没有能够分出空来,尽管我曾经把照相机带进了病房,但也没能够记录下这难忘的场面,本想能够写一写病人的感受,但由于病人治疗期间实在太痛苦,而且经常需要转院,很难完整地听到他们的感受,也成为了我的一大遗憾。
我们一个月支援SARS疫区的医疗工作就将在今天结束了,SARS这个病魔从我们来的时候每天一百多例下降到现在的每天不足十例,我自己感到有着些许的安慰,这一个月北京所有医务人员的辛苦没有白费。
我们虽然撤下来了,但仍然有大夫被抽调出来,继续与SARS病魔战斗,接班的同志今天已经开始培训了,与SARS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由于我们一开始的疏漏和失误,造成广东的一个肘腋之疾最后竟成心腹之患,造成我国由南到北的大面积感染,造成许多家庭家破人亡,但是有医务工作者终于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和支持,我们的政府终于成长起来了,开始敢于直面困难,直面错误,直面百姓,果断地刹住了SARS的进一步蔓延,为这样的政府,我们去与病魔战斗,我们感到——值!
全国SARS的感染人数已经是一位数了。但今天却得知5月14日已经取消旅游警告的加拿大多伦多市26日又重新列入非典型肺炎疫情严重地区的名单;香港虽然解除了旅游警告,但最近四天仍然有医护人员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感染SARS;昨天我们医院门诊有一名SARS疑似病人竟然在候诊时逃跑了……虽然疫情得到了控制,但稍不留神,非典型肺炎(SARS)又可能肆虐,如果在今年下半年没有有效的手段,也许,我们还要回到SARS前线。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Lee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