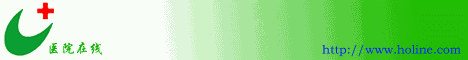 |
|
您想要的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
|
癌痛折磨其实能消除 吗啡是重度疼痛首选药物吴阶平院士曾说:“医生不单是治好病,更重要的是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 治疗疼痛,是对患者“生命质量”的一种保证。 “病痛”是个专门的词汇——有病就有痛,这是自然规律。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习惯了面对疾病时忍受疼痛的煎熬。而在疼痛分类里,癌痛是慢性疼痛里的一个专门分类,另一个是慢性非癌性疼痛。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900多万人患癌,每天有1500万患者在经受癌痛的折磨。世卫曾提出:到2000年,让全球范围内的“癌症患者无痛”。但今天看来,这个目标远未实现。7月30日,广东省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中心公布了目前国内癌痛治疗的进展情况:中国癌症患者有450万人,每年新发病人180万,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140万,其中51%至61%的癌症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美国南加州疼痛治疗中心的专家称,正是中国人对吗啡的“成瘾恐惧”和“忍痛文化”,让不少患者宁可在痛苦中挣扎,也不愿意接受止痛治疗。 癌痛让人死的心都有 今年春节期间,家住北京的贾老太呼吸开始变得不顺畅。起初家人以为是肺炎,给她买了中药。谁知,几十副药吃下去也不见好。更糟糕的是,老人开始觉得痛。最初是颈椎,慢慢扩散到肩膀和手臂。一天晚上,贾老太坐在院子里,突然感觉晕头转向,到医院一照片子,竟然是肺癌。至今家人还瞒着老人,没告诉她癌症已到了晚期,而且转移到了颈椎。剧烈的疼痛没有放过可怜的老人,并迅速攻陷了她的身体。采访时,记者不小心撞到了病床沿儿,老人立刻发出了呻吟。“那感觉就像是慢慢冲开的一样。先是颈椎那里疼,后来发展到肩膀,然后跑到胳膊。”贾老太告诉记者,最严重的时候,她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到最后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像是麻木了”,整天只能躺在床上,连路都没法走。因为“只要一坐起来,我的脖子就疼得受不了,根本撑不住脑袋”,甚至“一碰就疼”。那时候,贾老太没有几个晚上能入睡,老人的儿子媳妇轮流照顾她,不停地给她擦拭因疼痛而汗湿的身体。最后,面对母亲痛苦的呻吟和医生的“晚期肺癌”诊断,身为大夫的大儿子终于“认命”了,把母亲送到医院去做止痛治疗吧。只要不疼,只要能够开心地吃几顿好的,只要老人家能好过一些…… 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癌痛每天都在影响无数患者的生活。据世卫统计,50%的癌症病人有疼痛症状,70%的晚期癌症患者认为癌痛是主要症状,30%的癌症病人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我国的调查也显示:70%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难以忍受。与这个惊人数字相对应的,是癌痛给患者和家属带来的巨大折磨。 一个正在候诊的晚期直肠癌患者突然疼痛发作。在众人注视下,这名50多岁的男子脸色蜡黄、汗流浃背、浑身颤抖。他双手紧紧抓住轮椅,想让自己的痛苦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但是剧烈的疼痛令他徒劳无功——这是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的一幕。目睹此情此景,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在及时治疗的同时感叹说:“癌痛带给患者的不仅是痛苦,有时还是尊严的丧失。”对此,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罗爱伦教授也深有感触:“如果没有经历过,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那种痛苦。病人疼起来时,别说大汗淋漓、满地打滚,就连求医生‘让我死吧’的都有,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癌痛学组组长倪家骧还告诉记者,很多家属告诉他,由于家里人患癌,晚上经常要起来照顾,结果弄得第二天班都没法上。倪教授说:“癌痛影响的不仅仅是患者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癌痛,我们关注的不够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把癌痛治疗作为一个治疗项目来看待,我国也于1990年左右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罗爱伦教授介绍说,1982年,世卫提出了癌痛的三阶梯治疗方案:轻度一般可以忍受,能正常生活,主要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止痛药;中度为持续性疼痛,睡眠受到干扰,食欲有所减退,主要应用弱阿片类药物(如可待因);重度为睡眠和饮食受到严重干扰,疼痛加剧,需要使用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可以看到,在癌痛治疗中,药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宇光教授告诉记者,医疗目的吗啡的消耗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疼痛治疗水平的客观指标,此类药物医疗目的使用量越高,说明一个国家对疼痛治疗越重视,对生命质量越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人均吗啡使用量为0.01毫克/年,丹麦的使用量为我们的6500倍,美国为2800倍。现在随着技术和观念的进步,我国每年医疗目的吗啡使用量由10千克增加到了目前的250千克以上,差距明显缩小,但整体的疼痛治疗水平任重道远。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癌症病人能得到全面疼痛治疗的不到30%。倪家骧教授认为,在我国,大城市的癌症患者有一半能得到癌痛治疗,而小城市和农村能得到相应治疗的患者很少。过低的医疗目的麻醉药物使用量自然对应着过低的癌痛治疗率。 很多人对吗啡有误解 十几年过去了,为何我国的癌痛治疗水平还这么低?倪教授认为,首先是癌痛治疗未被纳入医保,选择的人自然少,贾老太告诉记者,这次进行疼痛治疗全是家里出钱,“给孩子添了不少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水平较低,他到地方医院去时遇到不少“不知道癌痛还要治疗”的医生,还有一些医护人员知道该治却不得其法,而在发达国家,止痛是肿瘤医生等专科医师考核的必须内容;其三是专门从事止痛治疗的大夫很少,疼痛专业的软件和硬件急需投入。 罗爱伦教授指出,这还不算什么,现在最急需更新的是人们的用药意识。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应用麻醉药品的顾虑较多。“吗啡”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毒品,会让人上瘾。这样的意识严重影响到对癌症病人的用药,主要表现就是“成瘾恐惧症”——将耐药和成瘾混为一谈。倪家骧教授指出,这种阻力首先来自患者和家属。“家属反对使用吗啡是常事,都说害怕患者上瘾”,但有些医务人员面对疼得满地打滚的病人,居然也抱着这样一种观点:现在能忍就少用点,免得上瘾以后不管事。对于这种现象,倪教授哭笑不得。 黄宇光教授指出,“耐药”是指药物作用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下降,必须通过提高剂量来达到原有的止痛效果,只要疼痛消失,病人可以成功停止药物治疗;而“成瘾”或称为“心理依赖”则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病人不管痛与不痛都对药物存在异常的渴求。黄教授说,成瘾的人追求的是大剂量注射后血液内药物浓度突增带来的“快感”,而现在使用的都是控释、缓释型口服药,作用持久均匀,不会带来这种感觉。孙燕院士说过,他治了一辈子癌症病人,还没见过吃药成瘾的。记者了解到,世卫三阶梯方案就明确指出,治疗癌痛时应注意5点要求,即口服、按时、按阶梯、个体用药和注意治疗副作用。美国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万余例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病人中,仅22人成瘾,而这些人都曾有药物滥用史。 在号称“欧洲最大医院”的德国柏林夏利特医院,记者采访了癌症治疗专家贝恩德教授。贝恩德教授说,目前,欧洲多家权威部门一致推荐:吗啡是治疗中至重度癌痛的首选药,口服是癌痛治疗的最佳给药途径。杜冷丁不能代替吗啡用于治疗癌痛,它只可用于短时急性疼痛,长期使用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毒性、肾脏损害等。 癌痛是可以治疗的 即使解决了对阿片类药物的不正确认识,还有层层“关卡”需要克服。在宣武医院,记者了解到,申请阿片类药物需要户口本、身份证、大病历等各种证明,完成一次申请,至少得半天。别说耽误了止痛,这种过程本身就让患者和家属觉得吗啡等阿片类药物“十分可怕”。在一些地方,申请此类药物甚至要“审查”半个月,结果发生了审查还没结束病人就痛死了,家属来要户口本作死亡证明的事。倪家骧教授告诉记者,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对吗啡类药品管得太严,时常耽误治疗;而基层控制不严,很多非法流失了出去。他认为,对于注射剂和针剂,应该严格管理,只在医院内使用,因为这是可能被成瘾者利用的剂型;而对于止痛主力的口服药,尤其是控释和缓释片,应该放宽一些,让病人更容易得到。罗爱伦教授也认为,不能因为个别不好的现象而对绝大部分真正需要止痛治疗的病人加以限制。 说到对癌痛治疗的评价,倪家骧教授说:“癌痛治疗反映了医疗观念更新的速度、技术更新的速度和医疗管理的水平,它是患者的基本权利。”倪教授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资金投入到癌痛治疗和宣传中去,比如加强对基层医疗单位的支持,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参考临床经验,鼓励投入更多资金。罗爱伦教授告诉记者,吴阶平院士的一句话曾深深感染过她:“医生不单是治好病,更重要的是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罗教授指出,随着“生命质量”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癌痛等疼痛治疗会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医学和社会意义。“我们应该推广这样一种观念,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一有疼痛,就应该去找医生。” 癌痛可以治——这是采访中几位专家反复向记者陈述的事实。除了药物治疗,倪教授表示,世卫的癌痛三阶梯治疗方案可以使85%癌症患者的疼痛得到有效缓解,75%以上晚期患者的疼痛得以解除。另外,一些新的微创治疗,比如通过CT定位引导,毁损痛觉神经等则可以达到持久止痛的目的。 采访结束时,记者又去贾老太的病房看了看。负责治疗的大夫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给贾老太进行的是微创神经介入镇痛治疗,先使神经恢复,调整身体,再毁损痛觉神经,彻底解决疼痛问题。贾老太告诉记者,邻床的病友刚刚出院了。“他来的时候疼得路都没法走,现在精神可好了。”老太太笑呵呵的,似乎对自己的康复也充满了希望。 ▲ ●《生命时报》记者 吴 翔 ●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 2006-08-08 第01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