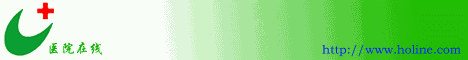面肌痉挛临床诊治进展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朱宏伟 李勇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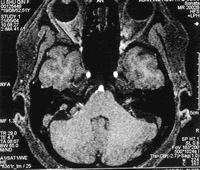 面肌痉挛又称面肌抽搐或半侧颜面痉挛,表现为阵发性单侧面肌的不自主抽搐——一种间歇、不随意、不规则的阵挛样面部肌肉收缩。面肌痉挛的治疗方法很多,目前多采用肉毒素注射治疗和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肉毒素注射治疗的优点是安全有效,可反复治疗;缺点是有效期短,以牺牲面神经的功能为代价,且不能纠正病因。微血管减压手术可针对面肌痉挛的病因进行治疗,能在缓解痉挛的同时,完好地保留面神经功能。 面肌痉挛又称面肌抽搐或半侧颜面痉挛,表现为阵发性单侧面肌的不自主抽搐——一种间歇、不随意、不规则的阵挛样面部肌肉收缩。面肌痉挛的治疗方法很多,目前多采用肉毒素注射治疗和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肉毒素注射治疗的优点是安全有效,可反复治疗;缺点是有效期短,以牺牲面神经的功能为代价,且不能纠正病因。微血管减压手术可针对面肌痉挛的病因进行治疗,能在缓解痉挛的同时,完好地保留面神经功能。
随着面肌痉挛相关基础研究的进展,微血管压迫学说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以此学说为基础的微血管减压手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自1977年国外研究者首次报告用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面肌痉挛以来,神经影像、术中电生理监测及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面肌痉挛的技术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有经验的治疗中心手术治疗面积痉挛的治愈率>90%。
术前影像学检查
面肌痉挛手术治疗前做神经影像学检查的作用有两个:①排除占位性病变;②确定面神经与周围血管的关系,指导手术操作,避免术中遗漏重要的肇事血管。该检查既能鉴别小脑前下动脉和小脑后下动脉等小血管(阳性率75.9%);又能鉴别椎动脉等较粗大的血管(阳性率100%)(图1)。
在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患者术前常规接受三维时间飞越法磁共振血管造影(3D-TOF-MRA),该检查除上述作用外,还可了解椎基底动脉系统有无解剖异常及神经上有无血管压迹。在面肌痉挛患者中,有48.6%的患者椎基底动脉向患侧偏移,而对照病例中仅13.5%有此现象。有无血管压迹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神经影像学检查在面肌痉挛手术治疗中有重要作用,但并非必不可少,MRI检查结果阴性的患者接受手术探查时往往也能发现肇事血管。在有多根肇事血管时,MRI有时也难以全部显示。
面肌痉挛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血管压迫本身不能完全解释面肌痉挛的发病机制。笔者在手术中发现,个别患者并没有血管压迫或其他异常因素,对这些患者仅行神经分离术后,其面肌痉挛即可完全消失。目前对面肌痉挛发病机制的认识是:血管压迫是面肌痉挛发病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一个条件可单独引发面肌痉挛,其他因素在面肌痉挛的发病机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尸体解剖发现,在60%标本中,小脑前下动脉形成的动脉环与面神经有密切接触,这个比例远远高于面肌痉挛的发病率。但约95%的面肌痉挛患者有明确的血管压迫。导致面肌痉挛的血管因素包括血管压迫的位置和数量,其中血管压迫的位置更重要,交叉压迫面神经根的血管比与面神经走行平行的血管更易导致面肌痉挛。
在微血管减压术后,大部分患者术前存在的痉挛症状和异常肌反射会立即消失,这表明,搏动性血管压迫是痉挛症状存在的必要条件,其可刺激其他面神经分支支配区域的肌肉收缩。此外,血管压迫还可造成面神经根损伤,此处产生的慢性逆向异常冲动会导致面神经运动核功能的改变,并逐渐在核内形成异常的神经环路,从而反过来引起面部肌肉的异常收缩。
术中电生理监测进展
微血管减压术常被用于治疗面肌痉挛,术后有5%~10%的患者会发生听力减退,甚至听力丧失,颅神经也可能受到损害。术中电生理监测的目的是在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的同时提高治愈率,术中使用电生理监测可有效避免颅神经功能损害。
电生理监测包括肌电图(EMG)、神经动作电位(NAP)、混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等。其中最重要的监测方法是BAEP和术中诱发肌电图监测,前者是为了避免手术对面神经的过度干扰,后者是提高手术疗效的有效手段之一。
BAEP监测是一种非介入性检查,在术中任何阶段均可进行记录,其可监测从耳蜗到下丘的整个听觉传导通路。BAEP对听觉通路的损伤非常敏感,在手术结束时仍存在Ⅴ波的患者听力几乎不会受损。术中引起BAEP改变的原因很多,包括听神经受到牵拉、压迫,及发生缺血或横断损伤,脑干内听觉通路受损也可引发BAEP的改变。在术中因牵拉小脑而使听神经受到轻度牵拉时,BAEP会表现出典型改变,即V波的潜伏期增加0.5~1.0
ms,改变小脑牵开器的牵引方式或手术方式有时可逆转BAEP的异常改变,但很多BAEP改变是不可逆的。BAEP与外科手术操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研究听力丧失的机制,从而提高外科手术水平并防止类似错误反复出现。
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可判断面神经根减压是否充分的监测方法。微血管减压术后,瞬目反射不会再引起口轮匝肌收缩。正常情况下刺激面神经的分支只能引起该分支所支配的肌肉收缩。很早前就有研究者就发现,面肌痉挛时会表现出如下电生理特点:当对面神经的一个分支施加逆向刺激时,在面神经其他分支所支配的肌肉上可记录到一个反射电位,电位的波幅为100~200
μV,潜伏期为7~10 ms,这种反应被称作“侧扩散效应(LSR)”,其产生机制尚不明确。在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中,LSR在全身麻醉状态下亦可存在(肌肉松弛剂对其产生有影响),整个术中均可对该指标进行监测。将肇事血管从面神经上分离时,LSR可完全消失;多数情况下,将肇事血管复原后,LSR会重新出现。微血管减压术结束时,LSR的消失预示着术后面肌痉挛症状将会消失。
对面肌痉挛患者实施微血管减压术的过程中行电生理监测的作用如下:①减少手术并发症(术中听觉诱发电位监测);②研究面肌痉挛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原理;③在手术麻醉状态下客观判断减压是否充分(术中面神经LSR监测)。面神经LSR监测可检出面肌痉挛的特异性波形,在实施有效的减压后,该波形将消失。此监测方法可克服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经验判断减压是否充分的缺点。
手术方法的改进
自1977年Jannetta首次详述了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的步骤以来,手术方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进,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改善疗效并减少并发症的问题。
笔者及其同事采取的手术方法为:在全身麻醉下,让患者侧卧,头部保持屈曲位,下颌距胸骨2指,头部以颈为轴向前旋转10°并保持水平位。术者可依据患者颈部的长短和自己的习惯选择切口方向,在横窦—乙状窦交汇处(可先在皮肤上标出横窦和两条腹肌沟的体表线,两者交汇处即为横窦—乙状窦角)钻孔,用铣刀切割大小约2.5
cm×2.5
cm的骨瓣,切割后骨窗呈方形,上达横窦下缘,前侧(耳侧)达乙状窦后缘。已打开的乳突小房要用骨蜡严密封闭。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可少量或间断使用脑压板,不宜使用固定式脑牵开器。以“X”或“┴”形切开硬膜,并将其悬吊起来。在手术显微镜下,将器械置入桥小脑角,轻抬小脑,锐性分离小脑延髓外侧池的蛛网膜,然后抬起小脑绒球小结叶,在面—舌咽神经解剖间隙直接暴露面神经根,并在此视野下辨别肇事血管,松解压迫神经的血管袢(图2)。对压迫神经的小静脉可在电凝后切断;对压迫神经的动脉,可将大小适中的Teflon棉垫入三叉神经与脑干之间(图3);对脑干重要引流血管的处理方法与动脉压迫时相同。应调整好Teflon棉的垫入位置,其应使血管与神经完全分开,而自身又不易脱落,但要尽量避免其直接接触神经。术前、术中和术后应使用面神经诱发肌电图进行监测,以确保在麻醉状态下充分减压。减压术结束后可用2个钛夹固定骨瓣,以避免术后局部颅骨缺损(图4)。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近5万例面肌痉挛患者接受了微血管减压术治疗,这种手术为微创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很小,但对医师的要求较高。尽管目前有各种各样的监测手段,但这些手段只能起辅助作用。手术疗效、安全性及并发症的发生率主要取决于术者的经验。国外较大型的医疗中心规定,神经外科医师在实施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50例的基础上,才可实施该手术治疗面肌痉挛。一般而言,术者积累100例以上的手术经验时,才能达到稳定而理想的治疗水平。
|